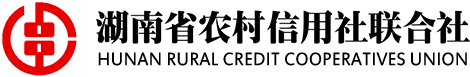童年散章(外二篇)
阳戏、碎花裙
母亲一下地,我就蹑手蹑脚地从院子里迅速转到大灶房里,乘太奶奶不注意,轻悄地推开母亲的房门,然后快步来到母亲的睡房。我就着屋顶亮瓦透来的微光,搬来床头放衣服的小木椅,摆在床前的木衣柜前,然后双脚踩上去,两只小手抓在木衣柜的最上面一层,稍微一抬头,那段白底蓝黄相间的小碎花布就入了我的眼。我用力踮起脚,伸手去抓小碎花布,抓住了再拖出来,裹进怀里,风一样地跑出家门,奔向英姑家。
英姑已在家等候多时了,见我进来,忙关上房门,迫不及待的问,“到手没?”“嗯。”我点着脑壳,兴奋地从怀里拖出小碎花布,和英姑一屁股坐在砧板上,摆弄起来。
我之所以冒险偷来母亲的小碎花布,完全是因为阳戏。
这几日,村里张大爷过80大寿,请了一小班唱阳戏的,我和英姑、玉儿每天都去听戏。阳戏唱的是《陈世美》,秦香莲的苦苦哀怜听得我们三人都簌簌落泪。英姑到底是年纪大些,她一听,就把唱词也记住了,散戏后,她竟然会唱一小段了。
小姐呀小姐,我的小姐呀啊……喔……
我本是呀啊,不忍心呀啊……喔……
奈何相爷来逼亲喔……
傍晚放牛的时候,英姑一唱,我和玉儿都觉得好听,于是就跟着英姑学唱。英姑唱一句,我和玉儿也就唱一句,从下午唱到黄昏。英姑突然起身,在我和玉儿面前转了一圈后,说:“我们也成立个戏班吧,就唱《陈世美》。”还不等我们说话,她就吩咐我妹妹和玉儿的妹妹去山上采集花草和柳条。英姑变戏法似的弄来一把小木梳子,给玉儿梳了个小姐头,再把妹妹们从山上摘来的花草一股脑儿地簪在玉儿头上。英姑簪的很细致,和阳戏班唱秦香莲的头饰差不多,大花簪在头顶,草叶簪在脑后。玉儿妆扮好了,给我妆扮就简单的多了。英姑把我的头发从正中间分成两半,使劲高盘起来,直接把两根长柳条插在高盘的发髻上。于是,我就成了陈世美。我极不乐意,给英姑说,“我不做陈世美,我要做秦香莲。”英姑斜我一眼,说,“你三大五粗的,没玉儿一点秀气,还想做秦香莲?让你做陈世美已经很不错了。”玉儿自然是一脸的欢喜。我狠狠地盯她一眼,开始准备唱戏。
英姑让玉儿先唱,让我站在一边陪衬着。这样的机会又不给我,于是,我决定整整玉儿。玉儿一出场,我马上吹眉瞪眼,露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玉儿一见,就格格大笑起来,怎么也不开口唱。英姑见状,只好指挥重来,而我依然逗玉儿大笑不止。这样来来回回重来了几次,都没达到好的效果。英姑急了,凶巴巴地对玉儿说,“你再笑就不让你当小姐了。”玉儿便呜呜大哭起来。
玉儿哭完,英姑还是没让我做秦香莲,我只好认真地唱陈世美。两个妹妹则分别成了我和玉儿的书童丫鬟。英姑还给我们设计了很多动作,大抵都是从阳戏班模仿来的。
开始,我们只在傍晚放牛的时候,躲在山上唱。后来,被村里其他的玩伴们发觉后,他们竟然出卖了我们,不上山的时候,他们也会跑过来,要我们唱给他们听。英姑是很豪爽的。一有要求,她就会安排我们唱。这样,村子里的大人们也都知道了我们唱戏的秘密。我们也就索性把舞台移到了玉儿家的岩塔里。只要不下雨,我们每天傍晚就会照唱不误。
我们的阳戏越唱越好,要求也越来越高。头饰用花草柳条可以代替,但是戏服成了英姑的心病。
很久以前,我就知道母亲有一块小碎花布。当英姑要我们一起想办法,备两套裙子做戏服时,我就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英姑。很快,英姑就给我想了个办法。
此刻,英姑把布看了又看,在身上比划了半晌,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。不一会儿,玉儿也来了。玉儿一来,英姑似乎找到了灵感,她立即用剪刀把那块小碎花布咔擦、咔擦剪成几大块,再把布块用针线缝制成圆筒形状。到傍晚时,英姑已经缝制好了两条圆筒裙子,我和玉儿一人一条,穿上后再唱《陈世美》。这一场,我和玉儿演得很投入,唱得很精彩,英姑在台下也随我们一起大唱。
小姐呀小姐,我的小姐呀啊……喔……
我本是呀啊,不忍心呀啊……喔……
奈何相爷来逼亲喔……
村上的男女老少都来看我们唱戏,还不时爆发阵阵掌声。
母亲是在我唱完《陈世美》卸妆的时候找到我的。母亲一来,英姑、玉儿马上就跑了。留我一个人,穿着小碎花圆筒裙站在岩塔里。母亲一言不发,死盯着我看了好久。我知道母亲很生气。太奶奶呼啦呼啦的喘着粗气从母亲后面跑来,一把抱住我大哭:“我的小祖祖呀,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呀,你把你母亲给你姑姑准备的嫁妆布拿了呀。”
母亲没打骂我。
不久,母亲让在信用社上班的父亲带我去他那里读书。开学前,我趁母亲不备,寻了个机会,去和英姑道别。一走上英姑家的泥巴岩塔,就看见英姑正在唱阳戏,身上也穿一条小碎花圆筒裙,跟我和玉儿的一模一样。英姑一见我,似乎很不好意思,忙往屋里躲了。我跑进她的屋,英姑马上说,我去叫玉儿来,我们唱《陈世美》吧,我让你当秦香莲。我一听,暗自欢喜,正准备开场时,母亲从对面的老屋里,唤起了我的名字,不得已,我撒腿跑回母亲身边。就这样,我演秦香莲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流产了。
后来,我再也没有唱过阳戏,秦香莲也成了我童年里一个残缺的梦。没有唱戏,当然也就再没和英姑、玉儿一起玩过,就算放寒暑假回家,我也只是安静的呆在家里看书练字画画。读初一那年,听母亲说,英姑被人贩子拐卖到河北。不久,玉儿也嫁到了香港。如今,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老家的县城里,犹如那场盛大阳戏落幕的时候,整个岩塔只剩下独自一人。不过偶尔的黄昏,我会想起她们,想起曾经唱阳戏的那段青涩岁月。
牛背上的王者
英姑的阳戏调一唱响,我就知道要去放牛了。忙三下五除二地把太奶奶炒的小半碗油炸饭灌下肚,迅速溜进母亲房内,抓两把生花生,然后一溜烟地跑开,边跑边把生花生往裤袋里塞。
等我跑到牛栏边,生花生刚好塞完。我马不停蹄地打开木栓解开牛绳,将卧在地上悠闲回嚼草食的大水牛赶起身,然后拼命拉出牛栏,再把牵牛的绳子挽成圈儿,弄成尺把长,或直接拉住牛鼻子,快步赶到村口小溪边和英姑会合。
英姑决定去草坪放牛。英姑说,草坪好玩些,可以练习弯腰、撇一字、踢腿。那时,我们正在组建阳戏班儿,唱阳戏需要这些动作。所以,我很赞成。之前,母亲是不允许我到草坪去放牛的,因为草坪面积不大,旁边都是稻田,放牛的人也多,我们家是头大公水牛,食量大,性子烈,草吃不饱就会跑到稻田里吃庄稼,招惹是非,母亲为此常被人骂。不过,和英姑在一起,我常会把母亲的交代抛到脑后。
沿着小溪,直接往前走,不用转弯,很快就到了草坪。
我们刚到草坪,隔壁村的军宝儿也来了。他把牛绳子全部挽到牛角上,然后骑在牛背上,任牛边走边吃。他骑着牛走到我们面前,嘲笑道:“放了那么久的牛,还要坐草地,连牛都不会骑,简直比笨猪还笨。”
英姑一听,怒了,忙从草地上爬起,牵来自家的牛,把牛绳子一股脑儿全部挽到牛角上,然后费力地爬上牛背。英姑家是头老母水牛,性子温顺。而且英姑天天放牛,牛也认得英姑,牛当然不会在乎英姑坐到她背上。所以牛照样悠闲的摇着尾巴,迈着步子,啃着草皮子,偶尔抬起头,摇摇耳朵,或忽左忽右地用角擦擦被牛蚊子咬疼了的肚子。这些动作,对牛背上的英姑构不成威胁。英姑得意地笑了,扭头对着军宝儿示威道:“这有什么难的,瞧,我不也骑得挺好的么?”军宝儿一楞,马上把矛头指向我:“那她呢?能骑吗?估计还是个笨猪。”英姑脸一红,大声指挥我说:“梅子,快上!”
虽然我家的牛是头公水牛,性子烈,但军宝儿那嚣张的架势,是让我和英姑看不惯的。所以不能让他小瞧我们。于是,在英姑的指挥下,我利索地把牛绳子挽上牛角,然后转到牛的右边,准备翻上牛背。可是,当我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上跳的当儿,牛突然发狂,猛抬起脑壳,张开四腿,甩开尾巴,吧嗒吧嗒向前方的稻田冲去。刹那间,只见一望无垠的稻田里,立即起了一道一米来宽的深沟。那沟一直沿着我家牛狂奔的方向向前延伸。抛在牛身后的深沟里,青幽幽的稻苗全部被牛踩得东倒西歪。整个场面活似战场,硝烟弥漫,惨不忍睹。看到这个架势,我吓呆了,大哭起来,英姑和军宝儿也惊呆了,都浑然不知所措。刚好三叔来看稻田,他见状忙冲进稻田,使劲将狂奔的牛制服。
牛是被制服了,伴随而来的,当然还有母亲的暴打。
从那以后,母亲将我的放牛权撤消了。没有了放牛权,我就很少和英姑一起玩了。英姑每天都要放牛。每当看见英姑骑在牛背上,唱着阳戏调,一路欢快地去放牛时,我就特别想和她一起去,也特别想骑牛。“我就不相信我不能骑牛,我要制服它。”我暗暗对自己说。
这样的机会很快来了。
一天,母亲带我去上山挖红薯,顺便放牛。有母亲的监督,我是不能乱来的,我安静地牵着牛去吃草,母亲则时不时地和我说话。隔壁伯娘一来,母亲就和她说话去了,我寻住这个机会,忙将牛赶跑,跑到远离母亲三四个小土凸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我把牛套在一棵大树上,套的绳子很短,短到牛脑壳都不能底下吃草的地步。然后手拿一根木棍,站在牛的右边,准备上跳。我打算牛一动,我就用木棍打它,让它乖乖听话。我刚把手放在牛背上,牛哞的大叫一声,啪的挣脱绳子,转过身子,脑壳一低、一摆,牛角猛然钻进母亲刚为我缝制的小碎花马褂里,哧啦一声,新马褂撕裂,我瞬间被挑上了牛头,挂上了牛角,坐在了牛嘴巴上。我顿时魂飞魄散,顺手抓住牛角死死不放,大声呼叫着母亲。母亲听到呼救后,风一样地跑来,边跑边叫着:“哇住 ,哇住。”
那天,我是被母亲从牛脑壳上取下来的,新马褂也没了。
没几日,我家就换了一头小黄牛。英姑和军宝儿打得火热,也不喊我玩,因为我不能骑牛。
那个秋天,我被父亲接到他上班的地方去读书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放过牛。
我终究没能成为牛背上的王者,童年就过去了。
滚珠车的奢望 ![]()
父亲在对面山垭的田埂上一冒头,我家岩塔里就立马安静了下来。
英姑、玉儿、军宝儿、玲子、耿耿快速跳下滚珠车,慌忙掀掉大木盘,提起方向盘,搬上车架子,风一样地抱头逃窜了,留下我和妹妹瑟瑟等着父亲的责罚。
父亲走上岩塔,看见崭新的水泥岩塔上滑出的滚珠车印迹,就明白他回来之前我们在做什么了。于是脸一黑,找来一根竹条子,喝斥我和妹妹跪下,用手指着我们的脑壳,说:“咋就这么不懂事儿哩,带一群乱猴子到我家新新儿里的水泥岩塔里滑滚珠车,看把岩塔滚成啥样子了,这岩塔可是刚修好的。”
父亲母亲为修水泥岩塔半个月没合眼,白天陪工人打水泥桨,晚上还要摸黑到邻居屋里喊人帮忙,张罗第二天的工人。然而正值盛夏季节,天气炎热,全村人都喊完了,也没几个人愿意帮我家忙的。最后几日,还是舅舅从母亲娘家喊来的人帮忙当工人的。岩塔一修好,军宝儿就说这样平坦的岩塔好滑滚珠车,不过,他一直惧怕父亲,所以很少到我家的岩塔里来滑。
我特别想要一架滚珠车,哪怕滚珠只有鸡蛋大,我都不在乎。我早就看好了,我家柴房里那几块木板,正好够一架滚珠车的料,再把太奶奶灶头挂催壶的铁勾把拿来做方向盘,一定比军宝儿的滚珠车要神气。但是,我是女孩子,没军宝儿胆子大,偷不来滚珠,所以一直没有滚珠车。
一天,军宝儿把我和玉儿叫到他跟前,说:“我要一个大点儿的滚珠做车子的前轮,你们谁能帮我偷一个大滚珠,我今后就让谁玩滚珠车。”其实,我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一个修理手扶拖拉机的地方,那里肯定有大滚珠。所以,当我再从那里走过的时候,就特别留神儿,总想趁他们不注意时,拿个滚珠出来。但是很遗憾,我一直没有寻到这样的机会。倒是玉儿很快把一个大滚珠交给了军宝儿,我不知道玉儿的滚珠是不是从那里偷来的,我只记得我当时好嫉妒玉儿,暗骂自己没用。
从那以后,只要我上晒谷坪,军宝儿就专门把他的滚珠车开在我面前,滑来滑去,快活地大喊大叫,甚至还让英姑、玉儿开滚珠车,掌方向盘,在我面前显摆。英姑和玉儿也挤眉弄眼的鄙视我,不要我和他们一起玩。直到我家的新水泥岩塔修好以后,他们对我的态度才稍微好些。
那天下午,我刚到晒谷坪,军宝儿破天荒第一次喊我:“梅子,你来开滚珠车吧,我来推你。”我立马跨上车,把双脚缩拢,放在方向盘的两边,双手握住那根铁勾把做成的方向盘,身子朝后微微昂着,任军宝儿在我的肩膀上使力推。瞬间,滚珠车呼啦啦地飞奔开来,耳边簌簌的风响,和着滚珠碰击凹凸不平的岩石发出的呲呲声响,激荡、冲击着童年狂妄的心。此时,我像个高傲的王者,八面威风地接受他们的朝拜。
后来,英姑和玉儿也来了。他们一来,军宝儿马上站在我身后的木架子上,命令英姑和玉儿推我们,就这样,我们沿着晒谷坪转圈圈儿,大声笑着闹着叫喊着,声音一浪高过一浪,直到火红的太阳彻底掉下山崖,我们才悻悻地回家。
从那以后,军宝儿就要到我家新水泥岩塔里来滑滚珠车了。军宝儿允许我开滚珠车。我想着父亲也不在家,玩了他也不会知道,就和军宝儿商定好了,只要父亲不在家,就在我家岩塔里玩。父亲不在家的日子,我们每天玩的都很疯狂。伙伴越来越多,我们玩的花样也就越来越怪异。后来,我们把滚珠车进行了改造,在原车架子上放置两块长木条,在木条上面放上我家最大的大木盘,这样就可以坐很多人了。掌方向盘和推车的人也基本固定了下来。一般是我和军宝儿掌方向盘,英姑、我妹妹、玲子……坐车,玉儿、耿耿等人推车。玉儿推车,是我的主意,军宝儿没敢反对。
父亲见我和妹妹不做声,气呼呼地将竹条子一股脑儿地砸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便大哭起来,我们一哭,惊动了太奶奶。太奶奶一边喊天,一边抱住我们,不让父亲打骂。父亲只好气得跺着脚走开。也许是父亲跺脚的无奈触动了我,我再也没有让军宝儿到我家岩塔里滑过滚珠车,虽然我很想玩滚珠车,很奢望有滚珠车,但是我坚决抵制他们的诱惑。渐渐地,过了段时间,也就不再羡慕他们了,我安静地看父亲为我买的书,听母亲讲着动人故事,慢慢长大。
父亲永远都不会明白,我为什么要答应军宝儿到我家新水泥岩塔上滑滚珠车。童年的心事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向父亲开口细说。我也没有给父亲道歉。初中毕业那一年,父亲突然给了我三个大滚珠,比军宝儿的滚珠要大好几倍。这让我很惊讶。然而,童年已经过去,我对滚珠车也不再那么迷恋和炽热了,所以一直没有把那三个滚珠组装成滚珠车。到如今,那三个硕大的滚珠依然躺在我儿时的一大堆玩具中。终究如此,但它依然是我童年最奢望的梦呵……
(作者单位:张家界农商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