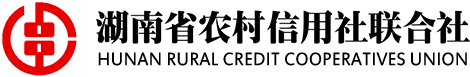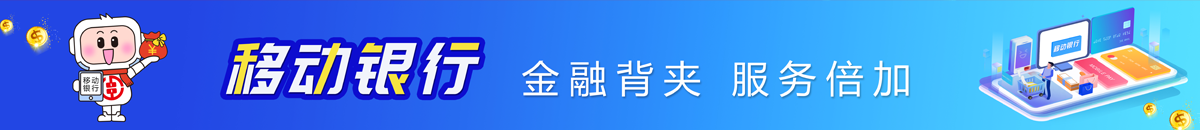读《瓦尔登湖》中的宁静
什么时候开始厌倦人群了。爱情上的求而不得?事业里的寸步难行?婚姻中的零碎苟且?还是人际关系里的虚情假意?风花雪月的热情随年龄增长冷却消退,面面俱到的周全在逢场作戏中节节败退,喧杂吵闹的生活在心气消散后显得残败不堪,那些规划的蓝图与现实的发展文不对题,幻想过的美好与自以为的期待南辕北辙,这时便明白离开人群也是一种难得的勇气。
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,什么才是真?笑容里的精心算计,关心里的指手画脚,道德里的好为人师,却很少有人真心问你一句“开心吗?睡得好吗?”网络时代里的跃进,人人都在春风似锦,为什么世界恰恰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?我们为什么要过着如此匆促的生活呢?这么多年的跌倒碰撞,难道还不愿相信人性就是幸灾乐祸的落井下石吗?
这时将自己的心绪小心翼翼收藏起来,《瓦尔登湖》里的哲学感悟简洁易懂,无法落地的欲望在书中的文字里逐渐萎缩,我们本来可以很简单的,文字所蕴藏的信仰反而衬的那些抑郁情绪格格不入。在生命中特定的岁月里,我们慢慢停下来,不想再只埋头赶路,也不想在周围人的看法里周旋。
梭罗说“我宁愿独自走我的路,或者可以的话,和宇宙的建设者结伴同行,也不愿混在盛装打扮的人群中招摇过市;我不愿生活在这躁动不安的、神经兮兮的、热闹喧嚣的、鸡零狗碎的世纪,我宁可站着或者坐着思考,任由它悄然流逝”,二十八岁的梭罗突然决定搬到瓦尔登湖,用最低成本生活在湖边的森林中,他用最简单的笔记形式记录生活,太阳的温暖角度,四季中的植物精灵,动物邻居的生活规律,森林里的小木屋装载了他自由自在的灵魂。他察觉到,生活的困顿,通常不是物质的匮乏造成的,而是源自人们不知餍足的欲望。
我们在流光溢彩的虚拟假象中待得太久,忘了我们人类自身也是大自然中的某个分支,我们将灵魂禁锢在钢筋里,给躯壳皮囊浓妆艳裹,却给阳光和空气贴上了廉价的标签,手机悄然摄取我们的心神,连放下手机安静睡觉都成了难事,精神上的毒瘾可比物质上的沉沦更为可怕。
我向往梭罗在瓦尔登湖居住时的心态,不必陷入浮躁的社交中,不必活成别人口中的自己,我想真诚地做我自己,正如他书中所说“我想要无拘无束地说话,就像清醒的人与其他同样清醒的人说话那样”。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到多余的东西,至于灵魂的必需品,是无需花钱也能买到。别给我爱,也别给我钱,给我真相吧,我不想空谈那些无聊而陈腐的道德观,也不想被金科玉律的条条框框束缚,当我说出“我不想”时,我的勇气已在内心扎根。
生活的节奏可以慢下来,道德绑架的关系可以不维护,得不到的执念可以断舍离,肤浅的扩张可以放下来,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,做我自己想做的事,不需要说明为什么,因为所有原则抵不过“我喜欢”三个字。
- 上一条:从《长安的荔枝》看农商银行的乡土使命 2025-07-16
- 下一条:没有了